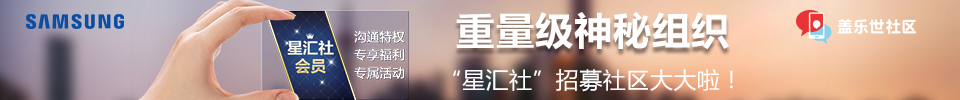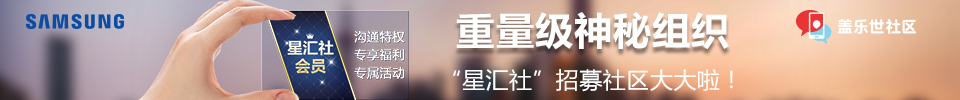灯会(灯会的由来和寓意)
那幅仕女图挂在父亲的书房里已经很多年了。
画中的女子低眉垂眼,手执长箫,一袭红裙曳地,素色的内摆上绘着鲜花。眼角抹着淡淡的胭脂,两襟掩映处,隐约露出的雪白领口宛如一线水痕。长长的衣袖垂落下来,袖口处,一只仙鹤翩跹欲飞。
年幼的他就这样伫立着,良久,仿佛自己也置身画卷一般,痴想着他遥远的霞光水影的梦。一直到后来的某一天,他才迟迟地意识到,或许是那时已近傍晚的缘故:斜阳,树影,老旧的书架,布满灰尘的房间。行将消逝的光线走进屋里,迟缓地,带着近乎哀愁的肃穆拥抱着墙上业已褪色的仕女图,仿佛一位老人。
一月快结束时下了场大雪。
房间里开着暖气。他从被窝里探出半个脑袋,揉了揉眼睛,转过脸看着窗外。猫趴在窗台上呼呼大睡,到处不见人影。天气预报里说,大雪要持续三天。部分道路被迫关闭,但地铁还能正常使用。
马路上开来扫雪车,黄色的警示灯闪烁不停。猫从窗台上站起来,打了个哈欠,又跳到枕头上,惬意地舔着爪子。窗外细雪纷飞,光秃秃的树干上满是白色。看了一阵,他厌倦了,翻过身背朝窗户,从猫手里抢来枕头抱进怀里。那种温暖的感觉使他一瞬间心旌摇曳。他看见猫踩着被子,轻捷地从他身上跨过,走到床的另一边。床头柜上摆着白色的灯具。
每到下雪的时候,四下里总是静极了。房间里光线沉郁。零星的睡意缠绕着他,他闭上眼睛,把脸蒙进被子里,任由视线里涌入暗色。半梦半醒之间,柔软的床面犹如一只女人的手,将他紧紧握住。他想起小时候曾在公厕边上看见的一株夹竹桃。那样阴翳的天色,黑色的树枝一点点茁壮着,犹如童话中伸向天空的绿藤……艳丽的花瓣在雨中泣开。他低声喊出她的名字。她抬起头,手腕停在空中,浅蓝的牛仔衬衣外面套着一间灰色开领针织毛衣,袖口挽起。握住不锈钢汤匙的手指修长白皙。乞丐模样的男人从公厕出来,踩在湿滑的煤苔上摔了一跤。凉风渐起。她低下头,小心翼翼地把碗里的面条挑进汤匙,抿着嘴不发出一点声音,领口微微敞开。夹竹桃满树的繁花就在水气弥漫的浑浊空气里缤纷自落。
忽然间,树上的鸟群惊飞四散。
他睁开眼,以为是有人敲门,仔细一看才发现是猫。窗外依然飘着细碎的雪花,行道树枯细的姿影不知何时悄然爬上床单。他坐在床上发愣。好一阵子,才慢腾腾地起来,掀开被单,走进厕所打理干净。又换上一身干净衣服。临走前给猫喂食,他想,那株夹竹桃大概已经不在了。
初春的街道上只有几个零星的行人。马路两旁堆着积雪,黑色的电缆宛如裂缝划破城市天际线。
约好见面的咖啡馆坐落在商业街的对面,既不崭新也不破旧,和成排的奢侈品商店遥遥相望。冬天里他每次路过,那种温暖并且洁净的气息总吸引着他,像是姑娘家疲倦地缩在沙发上抱着热饮欲言又止。他希望这里的墙上也能有挂衣服的架子。
推门进来,她已经等了好一阵。中午的时候雪停了,现在,傍晚的夕照落在作为装饰的书架上,用它行将消失的手指抚摸着那些无人问津的书脊。一排排低矮的建筑沉浸在落日余晖之中犹如木船在金色的大海上漂浮。水手站在屋顶上高唱着远航的调子,接着纵身一跃,跳下桅杆,径直穿过街道,走进咖啡馆里。
他要了两杯咖啡。
进门后,水手把旧外套挂在衣架上,摘下帽子,要了一杯朗姆酒。他坐到吧台前的高脚凳上,一面往嘴里灌酒,一面玩笑似的问道,漂亮姑娘们都去哪了。华灯初上,刚刚入夜的城市里游移着暧昧的光线。侍者端来咖啡。她挽起额前的刘海,凑近杯沿,说起元宵节那天有个灯会。所有的花灯都是仿古的,恰好这几天又下雪,一定特别好看……漂亮的姑娘呢?漂亮的姑娘呢?漂亮的姑娘们都去哪了?她还说,晚上指不定有汤圆吃。他有些敷衍地听着,一边把纸巾裁成方形,叠成纸鹤放进盘子里,又裁另一张纸。外面偶尔响起积雪压断枯枝的声音。来往的人们行色匆匆,嘴里冒着白气,他想着也许这就是马路上雾色弥漫的原因。
借着醉意,水手走出一段弧线,摇摇晃晃地来到窗边,向街上的行人挥手致意。漆黑的夜空中悬挂着一轮苍白的月亮。水手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他抬手抹了抹嘴唇,又醉醺醺地坐下来,出神地望着对面广告牌上那张女人的脸。
片刻,他回过神来,听见她说晚上的灯会要求穿古典样式的汉服。他忽然感到从小腹传来一丝凌厉的颤动。细雪霏霏,他依稀看见那座寂静的中式庭院里廖无一人。
小时候猜过灯谜吗?
他摇头,偷偷观察着她在玻璃窗上的侧影,小心不被她发现。侧影所特有的沉默使他不必担心自己的凝视太过深入,他看着她微微颤动的眼睛宛如进行一场注目礼。
摇摇欲坠的落日渐渐沉入夜的墓穴之中,几缕黯淡的光线在墙上映出一抹绯红。她岔开话题,说她昨晚又梦见自己去了喜欢的人家里拜访。不是什么节日,是生病探望。那个人的身体很不好。他回忆起他们第一次见面,她穿着白色的毛衣和灰色打底裤,眼镜是黑色的镜框。他拒绝了她。但后来,还是半推半就地答应了,约好在学校的地下停车场见面。很冷的冬天。北风穿过绵延的山脉吹向洼地,水泥浇筑的停车场里白炽灯涣散的光线有如一个病人,带着消毒水的味道离开幽暗的病床一步步走到他跟前。知道她喜欢纯色也是很久以后的事了。那天下午她摘了眼镜,戴一顶蓝色棒球帽,手里拿着相机。她让他靠在墙上,稍微朝右边侧过脸,自己则站在左边,调整光圈。快门发出几声响动,他听见有人走出电梯。几乎是出于本能,他回过头去看了一眼,恰好撞见她跪在地上一手撑住身体略微前倾寻找角度的样子,她的姿势让他联想到一张柔软的大床。暖气开得很足…窗外落雪无声。她靠在布满灰尘的书架上,咬住嘴角,头发被汗水打湿。凌乱的浅色床单,窗台上昏昏欲睡的猫。
休息一下吧。说着,她站起来递给他相机,空出来的手解开了领口的两只纽扣又擦了擦额前的汗。他把视线移向她胸口的位置,眼里立刻映入一片白皙。
想什么呢。她敲敲桌子,一手托腮。天气可真够怪的……她自言自语地说道,看向马路两侧的脏雪,一面搅动杯子里的咖啡。氤氲的热气升起来,雾蒙蒙的遮住她的脸。她抱怨着,说眼看着都快二月了,这雪怎么就下个没完没了。
阿姨把门打开。她说她看见那个人缩在被子里,闭着眼睛,很痛苦的样子。于是她走过去,探了探他的额头,印上一个浅浅的吻。阿姨掩上门,回到客厅的沙发上,她坐在地毯上等他醒来。风从窗户的缝隙穿过,搅动鹅黄的纱帘。她挪近了靠在床边。睡意袭来,她侧着脸趴在他的手臂上,望着窗外被雨水打湿的树叶慢慢合上眼睛。断断续续的声音传入耳中,那样凄恻,几乎是记忆式的,在她梦中回响。
她继续讲述着,他看见那座庭院紧闭的大门被谁推开了。四顾无人,他迟疑着走进院子。彼时大雪方停,白墙黑瓦的庭院里四处覆盖着一层兔绒般的积雪。拱门后面是一条青砖铺就的长廊。长廊沿着湖水蜿蜒,掩以朱漆,两排高高挂起的红灯笼倒影在大片大片冰封的湖面上,雪水顺着屋檐滑落。惊醒的鱼儿在冰层下穿梭游曳。他用手指敲击着长廊两侧的栏杆,看见湖心的石山上立着一座八角亭。亭子与岸边以石桥相连;飞檐重叠,桥下流水涓涓。他走下长廊沿着湖边漫步,困惑着这偌大的庭院里何以空无一人。
湖心亭东边种着好些常青的松柏,枯黄的草地上散落着零星的白色野花。垂柳的叶子早已落尽,那些爬满青苔的枝干如今被积雪所覆,瓷白青绿,错落有致地交织着,在微暗的天色下随风摇颤。这时候,院子里响起淅淅沥沥的雨声。又走了几步,月门后面隐约现出一道人影。借着傍晚晦暗的光线,他低头从月门穿过,看见被雨水打湿的石板路上那道影子单薄而纤细,散发出纸片般苍白的气息。影子的主人斜倚栏杆,手里提一只红灯笼,出神地望着湖面。灯笼映红了她的长裙。
停立片刻,他悄不做声地从背后靠近她,伸手揽在她的腰际。长裙柔软的面料温暖地将他裹住,他顺势把头埋入她的黑发。芬芳拂面而来,他恍然间想起夏日里鲜花盛开的草地。他咬住她的耳朵,手指微微颤动着,缓慢上移,爬进她雪白的衣襟。
醒来后,我们打闹了一会儿,然后一起弹琴。雨水敲打着玻璃,天色如晦,黑色的电线杆上泛起若有似无的潮气。四手联弹。阿姨端着水敲门进来,说好久没听见弹琴的声音了,这时他忽然转过来看了我一眼。
好疲倦。
雨仍然下个不停。庭院里夜色渐浓,屋檐下的雨珠缀成水帘滴落在暗色的湖面上,溅起一圈圈涟漪。他扳动她的肩膀,迫使她转过来看着自己;又捂住嘴不许她发出声音,解开她腰上的青丝束带。灯笼落在地上,滚了两圈,坠入湖里。他听见火苗嗞的一声熄灭了。越过她裸露的肩部,一丝青烟从湖面徐徐升起。她扭头看向湖边的垂柳,木偶般缺乏生气的脸上却泛起胭脂样的颜色。
远处是雾霭迷蒙的群山。他把她按倒在湖边,束发的丝带沉落湖底。雨水濡湿了她的长发,她躺在雪地上,失神地望着天空,素色衣袖同地面融为一体。他跪下来,掀开层层的裙摆,直到双腿迷人的曲线在眼前显露无遗。院子里雨声愈发激越。他把头埋进她的腿间。那种腥湿但温暖的气味俘虏了他,他贪婪地吮吸着有如沙漠中迷途的旅人。这时,一双柔软的手从后面悄悄地爬上他的身体。她抱住他,将他紧紧拥入怀中,咬紧嘴唇没有一丝声音。
好喜欢他。她坐在木桌对面,轻声说道,所以梦真是神奇的东西,不是吗。
湖面上,她漆黑的长发在水里四散开去,宛如墨色晕染。他疲惫地睁开眼睛,离开她的身体,看向对岸长廊上明灭的烛光。她喘息着,胸口起伏不定。稍顷,他低下头,脸贴在她的肚脐上,孩童似的抚弄她凉软的胸乳。
晚风吹过,水面上灯笼的倒影迅速黯淡下去,几近消失。庭院里的枯叶相互纠缠,发出沙沙的轻响。雨就要停了,他想。他伸出手,想要接住从屋檐上滴落的水珠,却忽然间被一股力量缠住。余烬重燃,她猛地翻过身子将他压在下面,分开双腿骑坐在他胸口。湿漉漉的长发绕过脖子,贴着身体的曲线垂落下来。仅仅一瞬间的光亮,他看见她的锁骨瓷器般纤弱皙清,素白的衣袖在烛火掩映下艳若云霞。这时候,火光熄灭了。黑暗里,他聆听着她呼吸的声音,眼前浮现出画中女子手执长箫的模样。艳红的衣袖上,一只仙鹤翩然欲飞。
……嘈杂的雨声渐渐止息。天色向晚,咖啡馆外的马路上亮起街灯,衣饰华丽的女子挽着男人的手臂在对街的商店里走进走出。她往嘴里塞进半块饼干,断断续续地说着,杯子里的咖啡早已凉透。她说梦啊,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不管醒来后多努力地回想,还是会一点一点地忘记。于是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记下前一晚做过的梦。她还说,有一天早上,醒来后她坐在床边伤心了很久,因为梦见自己错过了喜欢的人打来的电话。
后来,她又开始讲元宵节晚上的安排。赏雪,字谜,花灯……朱门紧锁,他站在台阶上,后知后觉地意识到那座美丽的庭院已经永远拒绝了他。四下里静谧无人。她站起来,离开椅子,给自己裹上围巾。透过流光溢彩的玻璃,他看见一个忧郁的倒影,神情近乎哀悼。
晚上,他洗过澡躺在被窝里,壁炉摇曳的火光在墙上波浪般飘忽不定。木柴燃烧发出轻微碎裂的声音。有人往里面添柴。海浪起伏着,暗蓝的海平线上,月亮升起来了,映照着空旷的甲板。水手醉醺醺地爬上桅杆,手里摇晃着空酒瓶,唱起远航的调子。他听见海浪拍打着船舷。水手被海水沾湿的外套在月色下熠熠生辉。
他从被子里往外看了一眼。猫趴在书架上,窗外飘着纷扬的雪花。浅色的床单将他同外界隔绝开来。壁炉的火光捻弱了,他缩回被窝里,躲藏起来。一个人影沿着楼梯潜行而上。锁甲,斗篷,兜帽下形成的阴影笼罩住那张模糊的脸。按剑的手压在身侧,穿过走廊,小心翼翼地搜寻。他捂住胸口,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大口地呼吸着,身体止不住颤抖。昏暗中,他从门缝里窥见那人的身影。他的手紧紧抓住床单。门被推开,房间里顿时灌入冬天饱含细雨的空气。他想起从前阳光明媚的日子,虽然刮着冷风,但杏树已经开花。那人一声冷笑,从背后掏出匕首,闪着寒光的刀刃在夜色里画出一道曲线,刺入他的胸膛。鲜血淋漓,他的胸口仿佛暮春的原野上鲜花盛开。后来,又一个起风的日子里,她来到墓前,手臂缠着黑纱。长长的裙子扫过草地,光线阴冷,空气里氤氲着雨水和泥土的味道。她挽起头发,望着那方小小的坟墓,沉浸在一种悠长的情绪里,然后弯下腰,留下一束新摘的杏花。
猫离开书架来到窗边。窗台上,米色的纱帘垂落下来,掩住窗外昏黄的路灯。她侧着脸趴在床沿上,疲倦的样子……他摇醒她,让她来床上睡。她揉着眼睛问道,现在几点了,然后爬到床上,褪去白色的睡衣。她掖了掖被子,手压在枕头底下,转过身去。他在背后轻声唤出她的名字,手指掠过她光洁的皮肤。他听见她迷迷糊糊地说,明早我们弹琴吧。他答应了她。他看见黎明时分烟蓝的天空,阳光斜射进来,自己坐在一架旧钢琴前,手指落在沾满斑污的琴键上,一边弹奏着,为她唱起水手远航的歌。一支缠绵哀怨的曲子。她的胸膛起伏就像大海。
母亲忽然进来,手里拿着一沓皱巴巴的纸。在你床底找到的,她说,你从哪弄来的。她把纸揉成一团扔到他脸上,他从地上捡起来,摊开,看见画上几个熟悉的女子赤裸着身体搔首弄姿。他低下头不敢说话。母亲用力一拍桌子,训斥他,跟着就呜呜地哭起来。她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这种下流东西只有坏孩子才看的。你还那么小,就学会了这些,太让我失望了。他怔怔地站着,母亲的话回荡在他耳边。他听见她不停地重复着,你太让我失望了太让我失望了太让我失望了太让我失望了……他也一道哭起来,把纸塞进酸奶盒子。
雪停了,月亮挂上树梢。猫跳到窗台上,看看外面,又转过来,古怪地望着他。
因为要留出时间准备晚上的灯会,他们约定四点见面。买好票,她把随身的背包存在前台,然后带着他穿过圆形的拱门,走进庭院里。她穿着一条黑色长裤,衬衣打底,外面罩一件羊绒开衫。他问她背包里装着什么,她说是衣服,他便不再追问。两人静默地走着,下过雪的天空彤云密布。曲折的回廊上,红色的塑料灯笼已经挂起来了,院子里满是脚印。靠近池塘的树林里堆着好些脏雪,岸边布置着花花绿绿的卡通灯饰。他眯着眼睛看了好一阵,问她那是什么东西。她顺着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有些尴尬地笑起来。她说那是十二生肖呀,没看出来?于是她领着他来到岸边。他这才发现灯饰上盖着一层厚厚的塑料膜,上面还写有某某传统文化公司的字样。灯饰背后零星地摆着几朵粉色和白色的假花。四下无人,她弯腰捡起一支,自言自语地说,也许到了晚上会好看吧。
灯会七点开始,庭院里静悄悄的,不少地方还立着闲人免进的告示牌。池塘边种着好些垂柳,枯枝上挂起纸灯笼,灯笼下面大大的福字在风中打转。雨水滑落枝头,她拉着他穿过月门,一抬头就看见湖面上暴露在外的白色水管。水管被几条红绳牵住,固定在水面的浮石上,绕过湖心的假山。山上是一间八角亭。朱栏高阁,檐角覆满积雪。她走在前面,下了石桥,招呼他过去。她告诉他,等到晚上亮起花灯,整个院子就会和现在完全不同。他点点头。冬日的云絮倒影在湖面上,碎裂的冰块之间露出一片黄色的天空。
渐渐响起雨声。
他们穿过花园,跑到屋里避雨。她靠在门柱上,一手按住胸口,喘着气抱怨道,这雨怎么说来就来,一点儿兆头没有。外面飘着细密的雨丝。他走过去,从后面替她摘下围巾,指尖扫过她的后颈。馥郁的香气将他围住。手指轻轻颤抖,男孩趴在地上,拨开蒙在木门上的塑料纸。温热的水汽从门后涌出。他嗅到洗发水的味道,雨点拍打在青石板上,发出碎裂的声音。
这时候,她忽然转身往后退了一步,问他想不想看自己穿上汉服的样子。他说想,她便把他按在椅子上,让他稍等一会儿,说完径直跑入雨中。
屋里只剩下他一人。他坐在椅子上,百无聊赖地朝着四周张望。空荡荡的房间里一头立着屏风,另一头是一张书桌和几只圆凳。面朝大门的墙上贴着两幅字画,字画中间吊着一盏青纱灯笼。雨势愈来愈大。他离开椅子来到门边,看见花园里满目萧索,地上铺满了枯枝败叶。
良久,她回到屋里,手里抓着背包,浑身早已湿透。她说幸好包是帆布做的,否则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一面擦着脸上的雨水,脱下毛衣,说她要换衣服了,让他转过身去,不许偷看。他转过去脸朝着墙壁,身后传来衣物擦拭细碎的声音。浓重的暮色漫进屋子,雨气里弥漫着花香。灯光闪动一下,姐姐尖叫起来,然后用浴巾遮住身子,甩了他一记耳光。她说弟弟你真下流真没良心,你太让我失望了。
转过来吧。
他转过去,一位红衣女子映入眼中。院子里回荡着绵密的雨声,她侧着脸,微微低头,长长的衣袖垂落下来,隐约露出的雪白领口宛如一线水痕。
犹在画中。嘈杂的声音渐渐散去,雨幕下,他依稀看见一树白花在院子东边的角落里悄然盛开。她叫他过去帮她理一下后领。他的手绕到她的耳后,贴上去,感觉到她温热的呼吸。青色的灯笼在风中摇曳。这时候,一只手轻轻地将他推开:
不能太近哦,我有男朋友的。
雨水打落了树上的白色花瓣。他紧张起来,听见牙齿打颤的声音,催促自己快些,必须赶在灯会之前……这样,就不会被人发现。
她尖叫一声,想要躲开。她说你干嘛,接着就被他捂住了嘴,拖到屏风后面。她惊恐地睁大眼睛,挣扎着,看着他解开自己腰上的束带。她用力掰开他的手说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我有男朋友了你怎么能这样,一面用脚蹬他的肚子。他将她抵在墙上,像剥糖纸一样脱掉她身上那件红色裙子,吊带掉落肩头,他贪婪地亲吻她的锁骨。昏暗中他看见她白皙的身体,因瘦削而浮现的肋骨怵目惊心,一根根宛如阳光下海浪的阴影。
他沿着湿滑的小路朝前走去,两侧满是泥潭和被足印踩脏的雪。山峦如墨,夹竹桃艳丽的花瓣在雨中飘零自落,空气里浮动着公厕刺鼻的气息。那个乞丐模样的男人蹲在门口,夹着半截烟屁股,冲他摇了摇头。雨水淋湿他的衣服,他汗流浃背地走着,看见远处的夹竹桃像雾一样慢慢消失。他抓过她的手,想要索求某种慰藉,手指水一样流淌着,划过他的身体。疲倦袭击了他。他仰起头,视线越过屏风,看见一只雨燕贴着池水低飞而过。
走廊里响起脚步声。母亲把一沓皱巴巴的纸扔在地上,他听见姐姐哭哭啼啼地说你真下流真没良心你太让我失望太让我失望太让我失望太让我失望太让我失望了。暖气机在外面隆隆地抽转着,他抱住她,像被流放的疯子,双手将她的后背紧紧锁住。只是越用力,她却离得越远。一切都无可挽回地衰弱下去。他悲伤地意识到,自己深陷巨大的泥潭之中,挣扎只是慢慢地耗尽生命。
不可能,不可能。他不相信。他让她握住自己,她半推半就地把手伸进去,先是一愣,跟着就笑起来。他说你笑什么。她刚想开口,他掐住她的脖子说,你闭嘴,是因为天气太冷。她笑得更厉害了。她说你就算打我我也要说,我男朋友比你强多了。
他扇了她一记耳光让她闭嘴,又换种姿势把她按住,手伸进裙子里。灯笼愈加激烈地晃动起来。他抬起头,依稀看见灯罩上写着一行小字,只是光线太暗了没法看清。他的手在层叠的裙摆下摸索,直到碰到一种生冷粗糙的东西。他停下来,掀开裙子,看见一条黑色长裤。她仰脸望着天花板,头发上沾满灰尘,发出断断续续的笑声。她说哎你就是个废物,太让我失望了。
耳畔传来爆竹的声音。
风停了。院子里飞来一只黑色的乌鸦,落在湖边的草地上。随后是另一只乌鸦。他放开她,走过屏风,来到房间中央。借着微明的天色,他终于认清灯罩上那几个歪歪扭扭的小字是一句错诗:孤远帆影碧空尽。这时,他忽然想到那种只在丧葬场合出现的歌队。白色的幔帐垂落四周,唢呐咿咿呀呀地吹着,窗外是漫天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