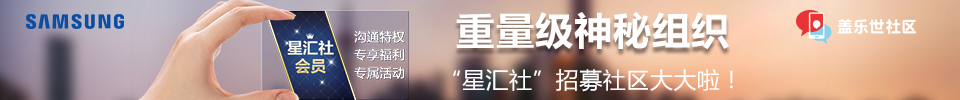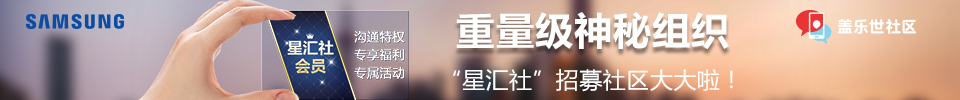吃人,太吃人了(吃人有错吗)
倒着看人,多半都要慨叹当年,几多风流,几多豪迈。
拉长了瞧,也能看出一个人所谓心之所好,志之所在,有几分真切,几分虚妄。
从九十年代的张艺谋到现在的张艺谋,他的步迹,确如他自言的,勤勉而不自我设限。
这无关作品水平,好坏本是任人品判,只是说每两三年的高产稳定,不负所言。

他的每一步,不说永远在中国电影潮头,起码也是略前一步。
直到环境改天换地,新人抢走风 骚,亦不为所动,其努力三十载的光华,似乎一成不变的样貌,容易让人们忘掉。
1950年生的张艺谋,而今已然古稀之年,在中国文艺界早慧者众,早衰者繁的背景下,其实非常难得。
作为电影学院78届的核心成员之一,说他的生涯是四十年中国电影史的浓缩,恐怕并非夸大之词。
他的突破与局限,隐没于历年作品之中,九十年代,因为巩俐,形成了一个以她为轴的清晰脉络。

如今女性、女权议题繁盛,当年的连续几作,都经得起,也值得这灼灼目光的重新审视。
借着刚结束的第十三届北影节的时间点,问世于1991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便值得再拿出来回味一番。


第一章 曲有别音
电影起手的配乐源自传统戏曲。
中国戏曲几经流变,各地开花,但之于受众,无非娱乐教化。
娱乐是价值观塑造,教化也是。只是正道之中有逆音。
单听《红娘》,是所谓突破封建男女交往的桎梏,但那演绎崔莺莺、红娘、张生的男女,又有几人能够超脱封建男女交往的规矩,这陈家大院里的三太太,就是一个明证。
一曲婉转,让人思绪万千,撩飞他处,然而此刻的急鼓急弦,却又是一剂醒魂凉水,在看似平静无波的房宅之间,搅动起惊天骇浪。

黑幕中出品与制片出现了两个对中国电影意义不凡的名字,邱复生、侯孝贤。
前者是台湾地区电影大佬,八九十年代的两岸,经济水平倒挂,文化传播的见识与通道,之于内地电影人,更是可遇而不可得,
如邱复生等人,亦如大量香港电影人一样,助力内地电影颇多,仅张艺谋在九十年代的几次创作,就离不开这位邱先生的支持。

片头年代电影公司,便在他的旗下运营。他在台湾地区解除戒严之后,帮助侯孝贤拍出了[悲情城市]。
当然说是帮助,按侯孝贤的话讲,这种“老板”并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只是不反对。
套用现在说网飞的段子,就是这样的老板,只给钱,不干涉你创作。
这样的老板也最有孵化器意识,早早就谋求内地电影人合作,便看中了张艺谋。

侯孝贤因关系密切,挂名监制也是自然。而且他认识张艺谋,更在邱复生之前。
因为他认识的第一个内地导演是吴天明,看的是他的作品[老井],而张艺谋,正是片子的主演和摄影。
虽然侯孝贤没有像历史小说中那样,说初见此人,便知不凡云云,但他说看[老井]时,哭得一塌糊涂——台湾影人这份“多情”,真是太普遍了。
所以,他挂名监制,丝毫不令人意外,借助[悲情城市]未退却的国际声名,也有利于这样的内地电影,闯荡欧洲——那一阵海外开拓,屡出此种故事。

不过侯孝贤也知道,创作路径相差极大,以他的理解,这样的家族故事,拍拍吃饭、聊天、女人心,是自然而然,但这是张艺谋的作品,有他自己的创作思路,因此侯孝贤并未真正参与拍摄。
而从2020年的平遥大师论坛张艺谋本人的回忆来看,即便侯孝贤真的履行监制之责,张艺谋也决计不会听从。

第二章 一镜殊途
只需翻翻《认识电影》之类的经典电影教材,也就知道镜头远近与信息量大小的关系。
比如拍的是人脸的特写,信息量最小,毕竟只有一张脸可供观瞻,反之,这种信息量的降低也可能带来表现力的放大,最极端的例子是德莱叶的[圣女贞德的受难]。

[大红灯笼高高挂]没有那么激进,它的第一个角色镜头,是一个正向近景,巩俐的两束花辫垂在两侧,一脸严肃和果决。
烛火中露出的部分衣服能看到民国女学生服饰常见的盘扣,这多出的一小截信息,为下一场的殊途做了最重要的铺垫。

镜头构成叙事力量的另一个可调动技巧就是长度。
在这个固定镜头里,光源来自镜头方向的右侧,它照亮了巩俐的整个脸庞,并在她的右脸(对观众这一侧而言是左侧)边缘形成一道更清晰的阴影,背景是纸糊窗,黑白分明兼之虚焦处理之下,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巩俐的脸上。
剩下的,就交给演员,巩俐为那个年代最出色的本土女演员,那一点点眼泪堆积并不算什么挑战,却也是让观众记住这张脸的闪亮时刻。

从理解电影的角度,她说的话,远比眼泪重要。
如果说一个规矩的世界是这部电影的骨架,那么那句“女人不就那么回事”便是它的血肉。
这不仅仅是比喻,情节铺排,正是处处血红。

母亲只闻其声,只知其言,却不见其人。
除了能够让叙事能量更为集聚,这个不可见的角色如果放在今天解读,或许是消解母亲意义的一个有力片段。
卖女为荣,以子求荣,此等故事,千年不绝,也渗入影片的骨髓。
真要母亲这个角色形容可见,便免不了要添上几 把干泪,反而让巩俐的眼泪失了盐份。
当然,这种隐字诀的极致,还是之后登场的陈佐千。

字幕再出,一个大大的“夏”字,春在何处是本能疑问,却还需要后文齐备,才能尽知其味。

传统的迎亲队伍,在一片喧闹中由近及远,逐渐消失在深景处。
而半路(画面右侧)“杀出”的主角,看清了全貌,一副民国女学生的打扮,而今却要嫁个有钱人,只是何以人单影只地走来?

此处便与苏童的原著,有了不小的差异处理,原著中,她是被那一群迎亲者带来了,而在电影中,巩俐走向我们,远离他们,这段姻缘结果的南辕北辙,近乎直白。



第三章 大院深深
坊间有言,张艺谋改编《妻妾成群》,外景却选了山西的乔家大院,令原作者苏童多少有些“不满意”,想一个南方庭院的封建往事,无论景、境、选角方向,都大异其趣。
如今再看,苏童写南,张艺谋拍北,这一南一北的呼应,反倒应应和中国女性命运的普遍性,反而愈发让人感到沉重。
而导演的理念,需要一个视觉设计来贯彻,对于摄影出身的张艺谋更是如此。
因此,[大红灯笼]是一个镜头感高度平衡,构图透视设计近乎计较的片子。

如果开头围绕颂莲的一近景一远景还其风不显,那接下来到了陈院,角色的走位被高度操控,门、墙、柱、壁等环境的应用,把一个逼仄、封闭的空间,圈锁在颂莲周围。
背对着古代汉语的女子在走着,仿佛那些字就是千年规矩的魂眼,注视着她走进一个原本应该叫做“家”的地方,仿佛这个叫做颂莲的女子,嫁给的不是一个男人,而是一个横亘在大地之上无数岁月的存在。

接下来,管家陈百顺作为第一个异性角色登场了。
颂莲站在下面,仰望着他。
他只是一个管家,可是他也姓陈,而把他高高托起的,正是陈家祖宅的威严。
在不曾认出颂莲是何许人也之前,他的语气俨然代表一个家族,代表一种无上必须仰望的权力。
而这一套东西,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又被诸如《大宅门》、《乔家大院》等影视作品,带着一种极度眷恋的情绪,重现着。
然而,[大红灯笼高高挂]终究有那么一点不同,它的大院是封闭压抑的,也是破败萧索的,在这一片陈迹之中,有一股强装的威严,也有一股显眼的朽败。
这也是镜头必须让颂莲慢慢穿过它的原因。
而今天的满庭尽是红灯笼,就是他日的满城尽带黄金甲,所差只是成本的投入。
但也是这种成本差,让那份衰落,更真实自然。
再下来,是另一个女性角色雁儿出场。她的眼神带着股傲慢与戒备,但是她在镜头中的位置(偏左)以及手上的活却泄露她的底。
这样的丫环在这样的深院故事里,都不可或缺,于颂莲,给有钱人家当姨太太是一种命运的萎缩,但对于雁儿,这却是命运的一次突围。
她的个性早早被这种注定的悲剧属性箍紧,挣扎得越猛烈,就越凄惨,但是她又必须猛烈,唯如此,才能在一个不属于她的舞台,争得自己的位置。
在这第一次同性角色互动中,我们也理解了颂莲那张耿硬的脸庞潜藏的狠辣,她的不客气,不只是陈家地位差的归位,更是两类人地位认知的确认。
此时,我们才发现,陈管家的引路,圈定的是战场,而战斗的双方,从来不是两性,而是一个女人与另一个女人。
在这样的战场中,是没有后来宫斗剧的同气连枝的,因为那提供了一种“HE”的可能,在真正的大院命运中,并没有这种选项。
第四章 挂灯敲脚
点题的玩意来了,就像后来黄金甲里气势宏大的摆菊花,点灯笼的镜头,以笔墨轻重,更胜角色。
那一招一式,一器一物,一挂一摘,一点一息,往好了说,未尝不是一种“工匠精神”,只是与社会伦理结合之后,里面中性的品格将发生巨大的偏移。
这些点灯人的中气十足,否则,不足以驾驭那看着新鲜的灭灯管器,同时,他们又是无声的,是所谓规矩的载物,没有自己的生命可言。
他们是规矩的器官,灯笼的一部分,面目可见,灵魂渺遥。
四太太的房间何其大。
娇小的太太、丫鬟们在里面,个个显得无比娇小,拉远的镜头更是将这种比例的对比更上一重。
老仆过来敲脚的一幕,已经是全片这个房间最热闹的时刻,却显得如此空旷,人在其中,微不足道。
有人说敲脚是欲望的修辞,确实有据可依。
之后陈老爷登场就大谈,脚敲舒服了,伺候人来,也更加舒畅。
只是,这种欲望不是这个女人,那个女人欲望的隐晦表达,正相反,敲脚跟点灯一样,将颂莲或者其她太太器物化。
颂莲的舒服是调教,这种调教不是激发她自身,而是为了更好地为老爷服务。
这敲脚的权利,便是权力的垂青,权力不垂青了,脚便敲不得,器化的停止意味着弃置。
在这样的关系里,不需要用冷落这等人性化的词语,因为颂莲们根本享受不到人的待遇。
把玩器物的陈老爷终于出场了,跟点灯人相反,他却是面目缥缈,灵魂狰狞。
这种虚处理作为一种技巧并不新鲜,甚至还有点风险——只是这风险针对的是商业。
彼时的张艺谋,还不必去面对那些。
但这种处理是合理与合适的,与影片整体的诉求高度匹配。也给镜头的距离感提供了继续下去的依据。
第二天,颂莲被管家领着领略陈家大院,这一行为先于拜会几位太太,顺位所展现的权力轻重便可见一二。
那些很无厘头地先祖垂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香火绵长的家族,无论满服还是汉服,却都是一种性别,那看不出章法的张贴甚至有一点讥讽意味。
在规矩支持的组织里,组织的规模和架构是由权力最大者掌握的,围绕在周围的力量,充满了不确定,这种不确定便带来横纵连横,试探攻击。
颂莲对前几位太太的拜会,让我们领略了组织内其她女性的面目。
大太太戏份少,无他,因人老珠黄。
虽然器化了女性,但女性毕竟不是真玉,愈盘愈佳,她终究抵不过岁月的残忍,但这自然属性却成了规矩的伦理基础,既然此物易老,自然需要定期更换。
二太太和三太太一冷一热,并最终与颂莲的关系反转,也是戏剧冲突制造的基本法门,舞台已就,演员也大致齐备了。
第五章 两场战争
规矩论还有一点余热要尽。
一则是雁儿被分配给四太太颂莲。
有敲脚的,就有硌脚的,这个丫环不贴心,就是让颂莲闹心的。
在这样的组织架构里,这种对抗是必然的,而颂莲和雁儿二三交锋透露出的个性,也注定了彼此的交锋无法善了,这是双重悲剧力量的推动,因此显得令人慨叹。
二则是这点灯规矩,到底意指为何?
原来不过是“翻牌子”之流。
用今天的话,就是形式主义,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形式即内容,你只要看看太太们的期望和失望就能明白。
所谓规矩,就是形式坚硬的内容,用在人身上,时间久了,必然僵化,待其僵化,个体的痛苦就越大,痛苦越大,人与人的斗争就越激烈。
乔家大院有两个空间,一个在地面上,一个在墙头上。
这乔家大院的墙头,风味跟[卧虎藏龙]里的高墙不同,到是与[邪不压正]里的北京墙头有点共同的趣味。
那是相对多一点的自由空间,也多一点天空的气象。
但天是灰蒙蒙的,空气是阴恻恻的,镜头也很注意不要把天空给得太多,“光前裕后”的匾额也如一道符印,封锁着女子别样的幻想。
灯点完了,拜也拜完了,仗则是要打的。
颂莲与梅珊的仗是热仗。
实际上,颂莲一个大学肄业女学生,是带着开化的自我意识,决绝地闯入这个她不愿闯入的世界的。
而三姨太梅珊是戏子,是旧世界规矩的一部分,她是这个世界的常客,这场热闹的剑拔弩张,其实颂莲从来没有占过优势。
真正击败梅珊的,是自己残存的那点对陈老爷的斗争意识。
而颂莲能够占据优势的,却是和雁儿的战斗,跟老爷不清不楚是早晚的事,雁儿也不是个善茬,但这个规矩圈里,姿色并不是资本——它只是一个媒介,骨血才是,这也是雁儿虽然闹腾,但终究期望要落空的关键。
也因此,颂莲并不是所谓的反抗斗士,无论小说原著还是电影,她都是悲苦女性之一,她不是什么大女主,开挂般地击溃了一个规矩的世界。
她能击溃的,只是一个有所幻想的丫环。
这个时候,那个自称一心向佛的大奶奶何尝不是一种幸运,规矩世界里的激烈斗争,已经伤害不到她,她熬过去了,是多么幸运。
第六章 楼台之上
苏童原著因描绘南方,大宅子里的恐怖意象是一口井,而山西的乔家大院里,则是一间弃宅,它位于那些灰蒙蒙的墙头之上,上着锁,里面蛛网密布,还有一双鞋。
这个巧合让我们可以引入西方文学中著名的“阁楼上的疯女人”。
当然,此刻的楼上,是一个个神秘的死女人。
这是健全规矩世界里,女性生存状态的重要一笔,疯了还是死了,不改命运的底色,这都是对抗规矩的代价,它同样也是一个“预言”。
巧示了颂莲与梅珊的命运,这就是人间吊轨之处,看上去她们彼此斗争,却终究殊途同归。
而疯女的一个所谓证据,就是行事不好揣测。
前半段和颂莲丝毫不对付的梅珊,在过了敲打阶段后,便立马转变了态度,成了真正向颂莲释放些许善意的,也是她。
梅珊的一袭红装是一种易于理解的个性展露,一切风风火火,率性而为。
对照之下,颂莲表面的各种强硬,反而有点色厉内荏。
打麻将在中国宅门故事里,始终都有文章做。
虽然[大红灯笼]的打牌戏远没有[色·戒]那般精妙、复杂,但高医生的出场,又补足了这个规矩世界里不可缺少的一种男性形象:看似儒雅,内有绮心。
这种P站禁忌桥段,我们实在太熟悉了,以致于梅珊的桌下轻撩,甚至有点滑稽——那个袜子。
在这场麻将中,二太太卓云的野心,在蒙太奇之下,也早就藏不住了。
老爷赤裸着,卓云表情亢奋,手指用力地为他按摩。
就在前一个镜头里,颂莲刚刚说,读书何用,不过是老爷的衣服,巧了,卓云很愿意成为这身衣服,为此心机深重。
但卓云的话语,透出比性欲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前文提及的骨血,想为老爷添一个儿子,这才是关键,是把自身更安稳地嵌入规矩世界的必走之路。
卓云的门清便显得雁儿的单纯,就算之后二太太的真心肠暴露,那一剪子的痛,也能转换为圈住老爷的新筹码,而真正的付出代价的,只有雁儿一人。
此处,我们需要提及又一个被“忽略”的女子,卓云的女儿忆真,她的镜头就那么一下下,就此退场,她是为所有这样的女儿退场,在这个规矩世界里,在这些女儿没有变成女人之前,她们无需有存在感。
第七章 何处见春
使性子和使计谋的怎么分,只要看看三太太和二太太。
颂莲的那一剪子,彻底把三太太的芥蒂消除了。
她和二太太的恩怨,总要有个机会说道说道。
话虽这么说,这一段面目揭露,也谈不上什么价值归位,正反分明。
二太太虽然阴鸷,却也是一种活法的选择,谁叫她没有像大太太一样,已经有了个儿子。
她的危机感,远比三太太和四太太高,只因那眉目间的皱纹,从不骗人。
既然骨血才是真正的筹码,以她的青春年少,这个赌局的赌注其实不大,回报却非常惊人。
不过她这场赌局唯一的问题,是她缺少“盟友”。
一个染红布没藏好,便落了个封灯的下场。
不过,这段假怀孕戏,除了又给了两个灯规:
点长明灯和封灯,似乎并没有给颂莲造成什么实质的伤害。
在戳破谎言的那一段,高医生一来,其实就藏不住了,但是所有人都在探口风,但是又没有谁把猜测或者事实说出来,他/她们都顺着一套规矩把这个注定的谎言破解流程走完。
相比于这种遮遮掩掩,之后老爷的辱骂更有意思,所有院中角色,除了小孩子,都立在门口,看着一场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的戏,直到封灯的规矩为这个坏规矩的行为画上句号。
这便是权力的面貌,事实还是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个环节都操控在老爷手中,然而老爷的谩骂与冷落又只是一时的。
毕竟,假怀孕不代表不能怀孕,欺骗是争宠,却不是背叛,权力在这样的欺骗面前,反而更加从容,操作颇多。
这个事件积累的负能量,是通过其她人的命运,被释放出来的。
所以,后面颂莲与雁儿的激烈对决,老爷并不在家,但老爷又何曾离场,这是剧本处理颇值得玩味之处。
既然说到剧本,我们便可切入影片的结构。
夏-秋-冬-夏,观众大多立马注意到“春”的消失。
这种文字点题,也是形式主义的一部分,虽然我们能从颂莲等人的着装中分辨出时间的推进,但四季变迁,从来不只是时间的标记,更是一种人生处境的隐喻,它浅白,也果断,没有一丝拖沓。
虽然之后内地这类作品多半都是篇幅绵长的电视剧,但有一部[大红灯笼高高挂],便能证明,如此线头纷繁的故事,是可以用电影有限的篇幅,浓缩其中的,亦如苏童小说所做的那样。
第八章 终成疯女
从一小时十七分钟开始,故事入“冬”。
大儿子飞浦完成了他的第二场戏——之前一场是笛声对她的吸引。
在这个异性身上,本存在着一种男女之事更寻常的可能,但因为他也是这规矩世界之人,这可能便也是没有的。
但生日宴上一把推开他的,也是颂莲自己。
由于视角的问题,这段戏的叙事意义其实不算太突出,尤其相比于苏童原著,从男性视角挖掘出的惨淡——飞浦说女人太可怕,似乎更具深度。
电影坚守一个视角,如果面对的是陈家、规矩这种形式般的存在 ,力道十足,但面对具体的人,尤其是在最后的助推时,便显得弱了一些。
回到颂莲这个人,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这只是第一层,在“光前裕后”的那场对话,则扒出了第二层,她和谁都格格不入。
因雁儿之死,她看透了这个世界,但即便如此,她还是不太会说话。
三太太梅珊以游戏人间劝慰她的结果,却是她一句话戳了她最不能为外人道的罩门:与高医生的恋情。
表面上看,她一时醉酒,在二太太面前脱口而出时,是无心之过,并不自知。
但是仔细琢磨,颂莲从未真正回应梅珊的相对善意,在她一副看透模样之余,梅珊的话摆明了是再度结盟的暗示,一起对付二太太。
然而她话锋一转,谈及高医生,或许真无威胁之意,却让三太太如何泰然。
于是乎,所谓杀鸡儆猴,猴没有儆到,又把三太太搭了进去,这或许就是看透与通透的区别。
之所以要解读这么一出,便是要呼应影片最后,颂莲终成疯女人的段落。
她为什么会疯,片子是留下一点点想象空间的。
在冬这一幕,雁儿和梅珊,都不是她想要置于死地的人,却都因为她的行为而死,所思所想与所作所为之间的巨大落差,无疑给了她巨大的刺激。
她醉酒的时候,说自己不蠢,只是一时算计,败了她人。
但这算计一错在错,她自己败了也就罢了,却把几条人命账,至少划了一笔在她身上。
尤其是她目睹梅珊之死,是最后那根稻草。
梅珊身死之后,她用留声机行妖鬼事,吓了陈家人,但在她心里,梅珊又会不会来找她呢?
这斗也斗不过,活也活不来,死又死不掉,念天地悠悠,除疯魔一般,又能如何?
来年灯笼依旧,人事全非,五太太又能知道些什么,唯规矩而已。